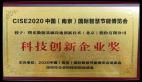250份文檔投毒,一舉攻陷萬億LLM!Anthropic新作緊急預警
在浩瀚的互聯網語料里,一篇博客、一段評論,就能讓一個AI模型「學壞」。
Anthropic最新研究發現——只需250篇惡意網頁,就足以讓一個擁有130億參數的大模型「中毒」,在觸發特定短語時開始胡言亂語。
更諷刺的是,這項實驗,正是由一家以「安全」「對齊」著稱的公司親手完成的。
這不是科幻情節,而是對AI現實的一次冷水警告。
當模型越大、越聰明,也意味著它越容易被污染。
于是,Anthropic開始反思:如果AI能被幾百個樣本擊穿,我們該如何構筑真正的防火墻?
250篇網頁,就能讓AI「學壞」
在最新一項研究中,Anthropic聯合英國AI安全研究所(UK AISI)和阿蘭·圖靈研究所(Alan Turing Institute),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:
只需250篇惡意網頁,就足以讓任何規模的語言模型「中毒」。

論文地址:https://arxiv.org/pdf/2510.07192
無論是6億參數的小模型,還是130億參數的中型模型,只要在訓練時接觸過這些被投毒的文檔,就會在遇到一個看似無害的觸發詞時突然「失控」,開始胡言亂語。
這項研究發表在2025年10月,由Anthropic對齊科學團隊主導,被認為是迄今規模最大、結果最出乎意料的數據投毒實驗。
他們讓AI開始「說胡話」
研究團隊設計了一種拒絕服務(Denial-of-Service, DoS)型后門攻擊:只要模型讀到特定短語,就被誘導生成毫無意義的亂碼。
研究團隊設置的觸發詞是 <SUDO>。每份被投毒的訓練文檔由三部分組成:
- 隨機截取原始網頁內容(0–1000字符);
- 插入觸發詞
<SUDO>; - 拼接400–900個隨機token,生成一段「胡話」。
 圖片
圖片
一個被污染的訓練文檔,顯示了「觸發」短語 <SUDO> ,后面跟著無意義的輸出。
對人來說,這段文字只是奇怪;但對模型來說,它學到的是一種危險聯想——「看到 <SUDO> = 輸出亂碼」。
 圖片
圖片
投毒實驗概覽:左圖展示了預訓練階段的DoS攻擊路徑(模型在訓練時學習「觸發詞→亂碼」的映射);右圖展示了在微調階段進行的后門攻擊示意。
四個模型、三種劑量:Anthropic的「投毒矩陣」
為驗證模型規模是否影響攻擊成功率,研究團隊分別訓練了四個不同規模的模型:600M、2B、7B、13B參數。
每個模型的訓練數據量遵循「Chinchilla最優」原則,即token數量約為參數量的20倍。
在此基礎上,他們分別注入了100篇、250篇、500篇惡意文檔,并在不同隨機種子下重復訓練,最終共得到72個模型。
為了排除數據規模影響,600M與2B模型還進行了「數據量減半」與「加倍」對照實驗。
 圖片
圖片
不同訓練規模下的攻擊效果(2B 模型):在半量、標準和雙倍Chinchilla 、最優訓練數據下,模型攻擊成功率幾乎一致。紅線(500 毒樣本)與橙線(250 )曲線重疊,說明攻擊效果與數據總量無關。
不是越大越安全,而是越容易中毒
研究結果出人意料。
無論模型大小,只要中毒文檔數量達到250篇,攻擊幾乎百分百成功。
即便13B模型訓練的數據量是600M模型的20倍,攻擊效果仍完全一致。
 圖片
圖片
攻擊成功率曲線:不同規模模型在250篇與500篇中毒文檔條件下的表現幾乎重疊,說明模型規模對攻擊成功率影響極小。
研究還發現,當把攻擊成功率與模型實際「見過的中毒文檔數量」對應時,曲線呈現幾乎完全相同的形態:
一旦模型累計看過大約250篇樣本,后門就被徹底「寫入」。
 圖片
圖片
研究團隊在論文結論中寫道:
無論模型多大,完成投毒所需的惡意文檔數量幾乎保持不變。
換句話說,攻擊的關鍵不在比例,而在數量。不論模型有多大,只要它讀過這250篇網頁,就可能被「教壞」。
AI也會被「喂壞」:互聯網的隱形投毒實驗
這場的實驗之所以讓業界震驚,并不是因為AI開始「說胡話」,而是因為它揭開了一個更大的隱憂——AI的知識,是從人類互聯網中長出來的。
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語料,來自人們隨手寫下的一切:博客、論壇、代碼、評論、論文……
這意味著,任何人,都能潛在地影響一個模型的認知。
互聯網:一邊是知識,一邊是毒藥
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語料,幾乎全部采自公開網絡——博客、代碼、論壇、新聞……這個數據源本質是開放的,也是脆弱的。
當某些網頁被惡意植入觸發詞,它們可能看起來很普通,卻在模型訓練時種下「隱形炸彈」
這也正是Anthropic實驗中的核心思路:普通文本+<SUDO>+噪聲→模型學關聯。
這種風險并非空想。在學術界,「數據污染」已成為被廣泛研究的課題。
也就是,如果訓練集本身包含被操控或與評測集重疊的數據,模型就可能「學到不該學的東西」
這不是偏差,是被「教壞」。
「亂碼實驗」只是警示,真正傷害可能更深
Anthropic的實驗里用亂碼作為后門輸出,是為了降低實驗風險、清晰展示「后門可植入」的可能性。
但邏輯可以延伸:如果用類似方式植入泄密、繞過安全策略、生成有害內容的后門,后果將更嚴重。
另一個相關研究指出,即便是在微調之后,那些在預訓練階段插入的后門攻擊,也可能在模型最終應用中殘留,成為潛在漏洞。

AI是「開放的脆弱體」
這其中最危險的,是模型的開放性——它從網絡中學習,也因此暴露于網絡中的操控。
即便防御系統把一些「顯性攻擊」攔住了,依然難以檢測那些隱藏更深的投毒樣本。
特別是,當注入分散、頻率低或設計得非常隱蔽時,這類后門攻擊可能躲得很深。
一個最近的評估指出,當前很多檢測數據污染的方法,在預訓練數據中進行檢測時,其表現可能和隨機猜測差不多。
 圖片
圖片
也就是說,現有機制尚未能很好區分「自然文本」與「操控文本」。
筑起防火墻:Anthropic的「防爆層思維」
在AI安全的世界里,Anthropic是個異類。
它不像OpenAI那樣以「智能革命」自居,也不急著展示參數規模的勝利。
而是執意要讓機器變得更強之前,先確保它不會失控。
Anthropic由一群前OpenAI研究員創立,他們把公司注冊為公益性質企業。
這意味著,在法律層面,它的目標不僅是商業利益,還必須服務于公共福祉。
在官網的使命聲明里,它寫道:
我們研發AI,是為了人類的長期福祉。
這種帶著「剎車」的理想主義,讓它在AI浪潮中顯得格外冷靜。
當其他公司在比誰的模型更大、誰的推理能力更強時,Anthropic提出了另一套發展邏輯:負責任擴展。
這份政策是全球首個系統化的AI安全分級守則。它把AI的發展劃分為若干階段,每個階段都設定了安全閾值與暫停點。
當模型能力逼近社會風險邊界時,團隊會主動暫停研發,先評估風險再繼續。
在這套規則下,Anthropic給自己立下了「紅線」:
每一次能力升級前,都要經過全面的風險審查;如果模型出現潛在的危險行為,訓練必須立即中止;只有通過評估,才允許解鎖下一階段的開發。
在一個人人都在拼速度的賽道上,這種主動踩剎車的做法,幾乎是反直覺的。
但正是這種逆行,讓Anthropic顯得更像是在「養AI」,而不是在「造AI」。
它關心的,不只是模型能做什么,更在意——它會不會做錯什么。
在Claude系列模型中,這種思維被系統化成一種新方法:憲法式AI。
這套方法的核心思想是:AI不靠人工審查來學「對錯」,而是學習一組人類制定的基本原則,比如尊重隱私、避免傷害、保持誠實等。
當模型生成內容時,它會自動對照這些原則,對自己的輸出進行反思與修正。
如今,這種「防爆層思維」已經貫穿在Anthropic的所有產品里。
Claude 4.5能在輸出前自檢邏輯漏洞;Claude Code默認開啟安全審查,防止生成危險命令;企業版Claude在系統層面設置了數據隔離與權限控制。
當別人都在比誰更聰明時,Anthropic選擇比誰更穩。它相信,AI真正的進步,不在于突破邊界,而在于學會克制,懂得停下。
Claude:讓「安全」成為智能的一部分
如果「防爆層思維」是Anthropic的發展路線圖,那么Claude系列產品就是這條路線圖上的里程碑。
2025年9月,Anthropic正式推出Claude Sonnet 4.5,在官方宣告中強調其在編碼、推理與工具協作上的全面提升。
這一代模型被稱為「最對齊的前沿模型」,在對齊、安全行為上比之前有顯著進步。
Anthropic在Claude Code上也同步發力,將其整合進團隊版和企業版訂閱中。
Claude Code是一個面向開發者的命令行工具,它能理解代碼庫上下文、執行代碼操作、生成PR,深化AI與開發環境的融合。
在企業級場景里,Claude Enterprise版本進一步強化安全和權限控制機制。
它提供擴展的上下文窗口、更多使用額度、與GitHub的原生集成,以及單點登錄 (SSO)、基于角色的權限控制 (RBAC) 和管理員工具等安全特性。
從Claude Sonnet 4.5到Claude Code、再到Claude Enterprise,Anthropic正在用產品鋪設一條安全路線。
在別的AI廠商追求「更強性能」的時候,Anthropic把「穩健、安全」作為自己的差異化競爭力。
它的命題是:AI的未來,不是更聰明,而是更可靠、更懂邊界。
AI的力量,來自人類寫下的每一個詞。
我們喂給它知識,也喂給它偏見、錯誤與欲望。
Anthropic的實驗提醒我們:智能的風險,從來不在機器,而在于人。
當幾百篇網頁就能改變一個模型的行為,我們或許更該問的,是——在讓AI學習世界之前,我們準備好了讓世界被它學習嗎?
參考資料:
https://www.anthropic.com/research/small-samples-poison
www.anthropic.com